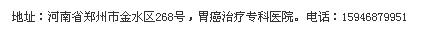沁源的绿,有多远
蒋殊
之前真没想到,去沁源竟没有高速。多次听说沁源的风情,多次有朋友邀请,却从来没有踏上那片土地。或许,内心深处觉得它距离很近。确实,它与我的家乡武乡同属长治市,相距只有75公里。可直到此次行至半路,才知道好长的路需要走国道。我惊讶地把这个信息递给好友,她笑:你以为哪里都像武乡那么牛?是啊,身在武乡这个老区,觉得已经是很贫困的山区了,竟还有不通高速的地方?一因太长高速有一段修路,于是走平遥下高速。司机说之后走汾屯线,就是汾阳到屯留的公路。路上大车小车摩托车川流不息。司机又说这是到沁源最好的一条路,只是晚上大车太多。于是知道,沉寂了几年的煤炭市场又好起来。一路以正常的速度行驶到沁源王陶乡镇上,堵车了。幸亏车上陪同的沁源政法系统女孩知道另外一条路,于是小心掉头,拐进所指小巷。尽管有不少像我们一样的知情者前往导致小小不畅,总体还好,顺利错过堵点。前行路上,司机不断给我讲述沁源的路,说着多年来不断争取却始终无法修一条高速的原因,这其中一个缘由便是可能破坏沁源的生态。我不懂专业,但觉得东西南北如此旷野,总可以有一处让沁源与外界相连。而就在这聊天中,我又得知沁源竟也没有火车。只有一截货运火车道,可以将煤运至沁县,再从沁县走大线运往全国各地。突然感觉,我将去往一个神秘的山里。继续前行中,司机告诉我,前面即将到达一座大山,开凿隧道的事也是起起伏伏多年不成。如果打通隧道,只有两公里,可现在盘山而上却有十几公里。说话间,盘山路到了,可惜天黑了看不到山路弯弯。上坡不长,便是一路下山。说是出山就快到县城了,再忍忍肚子晚点吃饭。可是下着下着,车速就慢起来,越来越慢最后再也走不动。再次堵车。路上散落着许多人,都是下来观望的,伸伸腿,还有放放水。司机经过快速打探,回来说堵车长龙茫茫看不到头,听说是交通事故。有车开始掉头。司机说现在只有花坡一条路可走了。我却觉得竟然还有路可走是极大的欣喜。但他说花坡路是土路,前几天刚刚下过雨,我们的轿车担心有路段过不去。可是等待无望,果断掉头。有路可走?不时有司机探头问。花坡路,他答。撤出堵点,发现掉头转向花坡路的有十几辆车,只有我们一辆是轿车,其余全是越野。说好的次日去花坡,可这个时间我来了。外面漆黑一片,看不到花坡一丝容颜。只觉得在静寂的旷野中盘山忽左忽右而转。想起小时候暗夜里回村路上,回家路上,一丝响动都让人心惊胆战。外面的夜里,有突然窜出的动物吗?有人烟吗?有坟墓吗?少年时与一个女孩从黄昏走到天黑,中途停留在一处林中玩耍,次日再次路经才发现那片树林是坟场。暗夜的山里,布满太多的未知与恐惧。车灯照亮前行路,只有光束所及区域是安全的。路边的小草有些惊。这样的夜晚,它们本该在睡眠,却没想到出现夜行人,呼啦啦惊醒它们沉睡的梦。它们睁大眼睛,好奇地打量着这些过路人,看庞大的车身如坦克般压过来,再扭动着远去。暗夜里所有都是恐惧。我们这些造访者,在那些静止生物眼中何尝不也充满惊恐?或许,远处正有一双或多双警戒的眼睛,忐忑地盯着这群行驶在弯弯山路的神秘夜行人。远远地,山下,燃着零星灯火,让我知道脚下有村庄。暗夜里的村庄总是很温暖。那温暖更多来自忽明忽暗的灯光。每一盏灯光后面,都是一个或多个人,而人是最能在这样的暗夜给孤独行路人以慰籍的,即便在遥远的远方,即便毫无一丝关联。唯有感觉人在附近,恐惧感才会消失。忽然抬头,前面出现了一束一束光柱。这是一处较为平坦之处,使得前面十几辆车同时出现在视野中。空寂的暗夜,突然不再清冷。这些本是陌生的车辆像约好似的,保持着几乎相同的车距,逶迤而行。二十几束散发着强烈欲望的光芒争相着要照亮前行更宽更远的路,大多数时候却都无奈扎进虚无的空中无影无踪。夜空如此强大,可以吞没一切。我们这些小心行进在山中暗夜里的人,渺小如正嘤嘤鸣叫的虫。尽管如此,视野中的十几辆车还是那么温暖。这些陌生的车,这个暗夜,这条曲曲弯弯的山路上,彼此之间就有了亲情。或许别的车中人不这么想,我却瞬间把每一辆车视为与我同行的亲人。有了这些同行者,有了前面忽明忽暗的一束束光柱,此行路上不仅不孤独,而且多了一些神圣的温情。长久的黑暗过后,远方终于燃起更多的灯火,那是永远没有黑暗的城市,也是永远没有神秘之所。心下踏实之际,却似乎失去什么。22:30,终于到达沁源县驻地,比预计晚了两个小时。太岳国际大酒店几个字出现时,我才恍然明白,我这个太行山的孩子,如曾经抗战年代那些战士一样,趁着夜色潜入太岳山中。二感谢好友邓焕彦,力邀我提前一天到达沁源。酒店大厅,若不是他大踏步迎过来,我都不敢主动迎上去。我们似乎有两年未见面了。而之前,也仅仅只是在一次采风中断断续续经历了三天行程。之后却成了再未见面的好朋友。我因事前来,只准备把首次来沁源的时间留给这一件事。他听说后却诚挚建议:提前一天到,看看沁源的风情。记不清这是他第几次邀请了。归拢了一番时间,决定听他的。其实一路上便与司机师傅几次感慨,这么不易的抵达,幸亏提前来了。邓焕彦的身边,是沁源党校校长梁晋峰。就是这位于我而言比较陌生的党校校长,成了我首次踏进沁源的邀约人。梁校长歉意满满,表达着我此行的不易。而我也发自内心说着歉意,为他们等我到这么晚。简单而盛情的晚餐后,他们说,好好休息,明天转转。并未描述的明天,在几个小时后来了。天有些阴,朦胧中出行。第一站是花坡。心目中,它已是老朋友。昨晚辗转路经,它似为蒙面的新娘。今日,我来揭去她的面纱。然而同样的路,却完全抹去夜里的痕迹。弯弯山路,看不出哪道辙印是我们深夜留下的,也看不出哪个村庄给过我温情的灯光,哪株小草受过我们车轮的划伤。换了天地。然而这崎岖不平的路依然亲切,如昨。不知什么时候,车外变了模样。世界杯刚刚结束,我却一次次疑似闯入绿茵坪。我是没有进过足球场的,可我心目中的足球场就是这样的绿,就是这样一整张盎然的绿,铺在一片土地上。也似上帝一双手,抖开一条庞大的绿色地毯,笼向这片叫沁源的大地。沁源的绿,原来是这般颜色;沁源的空气,原来可以这样深深呼吸?一路走着,感受着,却总是有些恍惚,有些疑惑。夏日,无论南方北方,都是满眼绿。可沁源的绿与北方的绿绝不沾边。来沁源前,我绝想不到我的邻县有这样的风光。此刻,目及之处除了绿就是无名的野花。花不夺目,却朴实得散发着天然而迷人的气息。我仔细看过,每一垄土地之间,都绿的无缝,连一片分界的泥土都不出现。多次问朋友,这是沁源田野的统一管理吗?农民不是总习惯将野草拔去吗?这里的野草,怎可肆无忌惮与庄稼牵手,蔓延成无边无际的绿海?车子行走在天然的大草坪中。抬头,山间云雾缭绕,突然想起贵州山中的风情,如入仙境。而细看,又异于南方那种钟灵,南方也见山,见土,而沁源的山与土为何这样大气,肯把地盘统统让给绿,甘愿默默隐身绿中。这绿,横行又霸道,横亘在沁源天地间。扑进传说中的花坡。在这里,第一次近距离看到风力发电机。它们在我眼里一直是风景,却总是远远的。如今,这随风转动的大风车高高矗立在花丛。从花中草中起身,仰望,它们犹如巨人。四野是一路铺出去的花海草海,如同我初次置身大海,茫茫没有边际。细看,这花坡并没有什么神秘的绚丽的花,无名的像到了任何一片田野,像回到我的家乡我的乡村,却又异于所到过的任何一处,这些不起眼的花花绿绿犹如千军万马集结在一起,列队铺开,便要让人惊叹自然的神奇,是上天专门赋予沁源这片土地的神奇。回望花坡路,坎坷间倒有了拙朴的美。小小花朵,朴素的让人怜惜。突然眼前一亮,不知是谁将一束花轻轻置于路边。那双手,一定是轻轻把这些花放下,因为它们依然一朵朵整齐偎依着。一定是一位女子吧,这样小心,除了敬畏花之美,还散发着采摘它们之后的一丝愧疚心。惊喜捧在手里。这束花,成了我的花。捧着属于我的一束花,在花坡轻行。预料中的雨还是来了,而我在花中才行进了几百米。先是淅淅沥沥,继而就大起来,成了雨帘,荡漾在眼前。幸而,下车时我带了一把伞。同行的朋友却没有伞,包括摄影师的相机都暴露在雨中。边回返,边抢拍下几张照片,把我的身影匆匆留进花坡的印迹中。站在伞下,看一场雨送来花坡的浪漫。果然,远处一对情侣,嘻笑着搀扶着从坡上跑下。男孩几乎是半抱着女孩,他不知在女孩耳边说着什么,女孩便开心地仰天大笑,雨水便顺势淌进她的红唇里。回望花坡,依然没有边际。在雨中,天际朦胧着,小花小草却清灵灵地欢叫。这是它们迎接润泽的时光。我带着花坡的雨水,以及泥土,草屑离开。当然,还有一束花。朋友叹,气候不好,未能尽兴看花坡。我倒有些满足。望不到边际的花坡,犹如一块铺天盖地从天而降的丝绸,而我,毕竟清晰捧起过它小小的一角。何况,无论是前来的路上,还是离去的行程中,一路的景致,何尝不都是花坡?三池上。这是中途临时改变主意要去往的地方。在我眼里,它比沁河源头,灵空山更有吸引力。路上,又遇大雨。走进一户人家,只一名60多岁的单身男人。灶台上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让人一下知道他是一个勤劳整洁的人。几杯茶水端给我们,又说喝杯酒吧,天冷。小小瓷杯放在灶台上,若隐若现的火苗映衬着,旧时的暖瓶,旧时的烧水壶,旧时的灶口铁盖,如一场穿越了时空的梦。那杯酒入了口,长久升腾在胃中的,就不仅仅是一杯酒的热度。雨小了些,继续池上行。朋友说池上是一个村,如今只生活着一位老人。我就是对这样的村庄充满无限想象与向往。一位老人的一个村庄,是什么样子?尽管,我曾经到访过三两位老人居住的村庄。朋友之前去过,他依然惦记老人,于是我们决定再次进入这个村。然而路途比想象的艰难。车走了很短一段就无法前行。石头刺啦啦划动底盘的声音让司机异常心疼。开头是遇到实在难行的路,我们下去走一段,推一段车。到后来空车也终于跨不过一块石头,我们索性下车,步行。一路上坡,一条只容一辆车经过的路。路边,依旧是层出不穷的野花,野草。有些识得,大多陌生。它们自古就默默生长在这山中,无人给它们取一个名。朋友也说不清几公里,他印象里很远。后来算算,应该不到四、五公里,但因为难行,走起来便特别漫长。但是一路花香弥漫。遇到一朵紫色花朵,竟缠绕着三只蝴蝶。就这样,大约一个小时后,被花与蝴蝶引上一处山顶。视野终于开阔起来。朋友指着远处的房舍开心地说:就是那里!这,不是又一处花坡吗?面前,依然是一片一片相连的绿。山坡上,小径上,散落着一片一片的花儿,草儿。一处矮矮的山头上一片密密的树,远处是一群羊。进村只有一条山路,路面上零零乱乱生长着泥泞的苦菜,车前子,毛毛狗,散落着大大小小的石头。村庄依靠的山上流动着雨后的云雾,与天相连。那片房舍面积不大,望过去大约十多个院子,全部是土坯房。青色的瓦因年久,已经幻化为沧桑的黑。一个个房舍,依然按照最初主人建造它们的模样,以村庄的形式一年年静守着这老地方。再近一些,往这些房屋的路上,已经长满杂草。一个老人,儿女或外人偶然的走进,怎能抵得过草的力量。于是,在大多数无人踏上的这条小路,草们便拓宽领域,野蛮生长。零乱的木材,几乎不再完整的房屋,坍塌的猪圈厕所,残破的平车,曾经欢愉此刻静寂的电线杆,便是这个村庄的全部。朋友边走近边嘀咕:老人家,还在吧?走过几处房屋,他一眼认出老人的居所。果然,这个院中的房屋尽管也是残破的,但屋顶却是与别家不一样的红瓦,也说明房屋在近年有过维修。墙由粗粗细细长长短短的木材围成,两扇门不到一人高,是经过几十年风雨的旧门板。院中屋檐下放置着大大小小的水桶,锅,盆。不必问,那是用来接雨水的。小时候每到雨季,院子里就是这样的风景。雨水,接来洗衣,浇地,有时候也用来吃。那时候没有自来水,井中挑水困难。如今老人一人生活,雨自然也是宝贵资源。“老人家,在吗?”朋友迫切走向正面房屋,边喊着。到了窗边,透过窗玻璃便看到老人,在炕上侧身而睡。听到来人,她起身招呼:快进来。灰色上衣,淡青色头巾,灰色隐约看到一丝格纹的裤子,腰间一条灰围裙。领子,袖口,围裙,都是零乱的。墙上是一块写着“心想事成”的墙画,炕上是被褥,枕头,衣物,甚至碗筷。地上也是,空间不大,挤放着凳子椅子,灶台,柜子,以及一口大大的水缸。一切都是零乱的。零乱,让一个人的生活显出生动。四世同堂的儿孙们满满挂在老人的墙上,温暖着她的日子。特别理解老人的心情,不想跟着哪个儿女迁到交通方便的村庄。不愿意和儿媳及孙辈们碰撞。风雨走过近90年,她选择了一个人的宁静。这样的村庄,仿佛世外桃园般宁静,纯净,美好。可是,这美好无比的村庄,只生活着一个人。老人说电话也坏了,儿女们忙,好几个月没上来了。连接她与外界的,更多的是村庄两个放羊人。我们在绿草如茵的白天说着话,我却总忍不住想老人的黑夜。还有,无人与她说话的白天,是不是也如黑夜的时光?离开时,腿脚不灵便的老人执意拄一根棍送我们出到院中。隔着矮矮的院门,老人,房舍,村庄,如此和谐安宁。沿路,那些无人居住的屋顶,瓦楞间,竟生出一丛一丛绚丽的花。长在屋顶的这些花有红有白有紫,与花下的藻,斑驳的瓦,瓦楞下依旧在剥落的墙皮,合围出一幅绝美的油画。不愿离去的地方,却是不适合生活的地方。返程中,遇到其中一个放羊人。当时没有羊,只他拖着一把羊铲从小路上逶迤而来。迎面,不知是因在寂寞的大山中长久沉默寡言,还是别的原因,交流有些困难。但他是我们在这个村庄看到的第二个人。而且,他也可能多次从山下老人儿女的手中接过日用物品背上这个村庄,送进那个矮矮的院门。举目,大自然那么美好,寂静的村庄在绿与雾的裹挟中更加盈润。这绝美的村庄,这绿菌如梦的大地间,这最该撒满生灵的土地上,竟然没有人。沁源的绿,颠覆了我对北方绿的概念,一路浸润着返程。我知道,通往沁源的高速,不远了。沁源的路,很快越来越好了。开心之际,竟也有一丝失落。返程到达沁县段时,视线里的风光让人猛一惊:哦哦,回到人间了。沁源,又远了。眼前,又出现平素的绿,平素的天与地。蒋殊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冶金作协副主席,太原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为《映像》杂志执行主编。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文学》《文艺报》《小说选刊》《中国作家》《上海文学》《北京文学》《中华文学选刊》等文学刊物发表作品。著有散文集《阳光下的蜀葵》《神灵的聚会》《百年长川》《重回》《再回》《沁源》。曾获“赵树理文学奖”、《小说选刊》年度大奖。《阳光下的蜀葵》《重回》分别进入、年全国农家书屋。作品收入中国散文、随笔年选及散文年度排行榜,散文《故乡的秋夜》收入年苏教版高中读本。本文系《环境与生活》杂志新媒体中心转载
自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官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