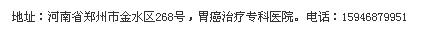翻译星星—沈晨天简介
沈晨天,上海交通医院核医学科,医学博士,住院医师,
中国医师协会核医学医师分会科信委科普与翻译组委员
师从罗全勇教授;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HopkinsUniversity)医学院联合培养博士。目前临床及科研主攻方向为分化型甲状腺癌诊治难点,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多项甲状腺癌相关课题,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青年基金一项、上海交通大学“转化医学交叉研究基金”一项、院级临床研究课题一项等。
甲状腺癌临床处理中的争议问题
(TuttleRM.ControversialIssuesinThyroidCancerManagement.JNuclMed,,59(8):-.)
由于目前尚缺乏前瞻性随机对照临床研究,有关分化型甲状腺癌(DTC)临床处理的推荐均依据回顾性观察研究,而这些研究往往不够完整,易有选择偏倚,还可能有所矛盾。因此,许多有关甲状腺癌临床处理的问题持续存在争议、尚无定论。该文围绕甲状腺癌临床处理中的3个重要争议问题进行了阐述:(1)单侧腺叶切除作为甲状腺癌初始治疗的指征;(2)术前颈部影像学检查的合理运用以优化手术的完整性;(3)I清除残留甲状腺组织(简称清甲)治疗、辅助治疗以及已知的持续或复发病灶治疗的选择。随着甲状腺癌的临床处理逐渐向更加依赖于风险分层的个体化推荐发展,医师和患者必须权衡临床处理的风险和获益,以达成一套优化且符合患者意愿/价值观以及当地医疗团队处理原则/经验的治疗方案。
甲状腺癌;放射性碘治疗;甲状腺腺叶切除术
甲状腺癌的临床处理已由原来的“一刀切”模式过渡到了“风险依赖”的治疗模式,包括手术范围、放射性碘(radioactiveiodine,RAI)的使用、促甲状腺激素(thyroidstimulatinghormone,TSH)抑制治疗的目标以及随访等,临床推荐均逐渐趋向于个体化[1-7]。过去,除了腺体内乳头状微小癌患者外,几乎所有甲状腺癌患者均接受了相对激进的治疗(甲状腺全切术加或不加预防性颈部淋巴结清扫、术后I治疗、长期TSH抑制治疗以及积极的随访评估)。但最近,美国甲状腺协会(AmericanThyroidAssociation,ATA)和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ationalComprehensiveCancerNetwork,NCCN)的甲状腺癌指南推荐均趋于保守(经过合理的评估选择后,有些患者可以进行观察随访、单侧腺叶切除且无需I治疗以及TSH抑制治疗)[1,5]。尽管这些相关指南的推荐均来自于有限的或有争议的数据,但目前该领域的发展现状(惰性肿瘤的低危甲状腺癌发病率逐渐增加,颈部超声用于治疗后随访逐渐取代了诊断性RAI扫描,术后I治疗越来越谨慎)使得临床医师不得不去反思是否所有原发肿瘤直径大于1.0cm的分化型甲状腺癌(differentiatedthyroidcancer,DTC)均需进行激进的治疗和随访。很多临床医师和患者更加倾向于采用高强度治疗(即相对激进的治疗方式),因为他们相信积极的治疗以及早期发现微小残留病灶可使预后更佳;而那些提倡低强度治疗(即相对保守治疗方式)的人则认为,通过合适的患者选择和随访,仍可达到类似的长期预后。低强度治疗的有效性主要基于以下假设:大多低危DTC患者预后良好,无论经过激进还是保守的治疗,疾病特异性生存率均可达99%,疾病复发率低于5%~10%;待病情需要时再行延期治疗干预(手术以及I治疗)并不影响疾病特异性生存;微小残留病灶常见,临床意义不大;早期诊断和治疗非常小的持续性或复发性病灶几乎无临床益处。
然而,比较2种治疗方式(即高强度和低强度治疗)的文献均为回顾性、观察性研究,缺乏前瞻性随机对照临床研究的数据。有趣的是,近30年来随着越来越多高灵敏度检测手段的临床运用[如高频超声、超高灵敏度甲状腺球蛋白(thyroglobulin,Tg)测定技术],临床对DTC的治疗手段更为激进(如:对肿瘤较小的患者行预防性以及治疗性颈部淋巴结清扫术;对生化提示疾病持续的患者多次行I治疗),但甲状腺癌的死亡率却保持稳定甚至略有增加[8]。由于存在不同的教育背景、临床观点、临床经验以及个人选择偏倚等,甲状腺癌相关领域的专家们即使阅读同一篇文献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有关甲状腺癌临床诊治的问题将长期存在争议。该文将围绕甲状腺癌临床处理中3个重要的争议问题进行综述:单侧腺叶切除作为甲状腺癌初始治疗的指征;术前颈部影像学检查的合理运用以优化手术完整性;I清除残留甲状腺组织(简称清甲)治疗、辅助治疗以及已知持续或复发病灶治疗的选择。哪种情况下行单侧腺叶切除才是甲状腺癌初始治疗的合理选择?
争议:是否所有原发肿瘤直径大于1.0cm的DTC患者初始治疗均应行甲状腺全切术。
立场1:所有原发肿瘤最大径大于1.0cm的DTC患者初始治疗均应行甲状腺全切术。因为完整切除可以能改善生存、减少复发、且术后可常规行I治疗,有利于随访中对疾病复发或持续存在的监测;如果手术由经验丰富的外科医师完成,手术并发症的风险可降到最低。
立场2:对于肿瘤最大径小于4cm且术前评估肿瘤局限于一侧腺体内的DTC患者,甲状腺全切术并不是必须的。原因如下:单侧腺叶切除与甲状腺全切后患者均可取得良好预后;单侧腺叶切除术的并发症风险低;某些患者还可以避免术后长期的甲状腺素替代治疗。虽然复发率相对略高,但随访中较易发现疾病复发者,且对这部分患者行补救治疗同样有效。
初始手术方式的选择这一争议主要围绕ATA指南第35B条推荐(表1),即允许肿瘤直径在1~4cm且无腺体外侵犯以及转移证据的患者初始治疗行单侧腺叶切除术[1]。尽管NCCN指南早就如此推荐,但旧版ATA指南曾强烈推荐肿瘤直径大于1cm的患者行甲状腺全切术[5,9-10]。旧版指南这样推荐主要基于几乎所有此类患者术后均需行I治疗,且这在年Bilimoria等[11]发表的研究结果中得到了进一步肯定,即肿瘤大于1cm时,甲状腺全切与单侧腺叶切除后患者的总生存存在统计学差异(10年生存率分别为98.4%和97.1%,P<0.05)。后续的大量研究表明,对肿瘤直径小于4cm的患者,经过合理的选择并校正重要的混杂因素后,2组患者的生存时间并未见明显统计学差异(表2)。关于这个问题的各种回顾性研究的细节在最新版ATA指南的正文中均有详细讨论。表1活组织检查确诊的滤泡来源甲状腺恶性肿瘤的手术方式推荐[1]
推荐编号
美国甲状腺协会(ATA)指南推荐
35A
甲状腺癌直径4cm,或明显腺体外侵犯(临床T4),或存在明显淋巴结转移(临床N1),或远处转移(临床M1),如果不存在手术禁忌,初始手术方式应采取甲状腺全切或近全切并切除所有可见原发灶(强烈推荐,中等级别证据)
35B
甲状腺癌直径4cm且1cm、且无腺体外侵犯、无淋巴结转移(临床N0),初始手术方式既可以选择甲状腺全切或近全切除,也可以选择甲状腺单侧腺叶切除。甲状腺单侧腺叶切除作为初始手术方式对于低危甲状腺乳头状癌或滤泡癌可能是足够的;然而,结合临床病理特征及患者意愿,仍可行甲状腺全切,以便于术后I治疗的开展并有利于随访(强烈推荐,中等级别证据)
35C
如对甲状腺癌直径1cm、无腺体外侵犯且无淋巴结转移(临床N0)的患者行手术治疗,则初始手术方式采用患侧腺叶切除,除非存在需切除对侧腺叶的明显的指征。如果既往无颈部放射史、无甲状腺癌家族史、无临床可探及的颈部淋巴结转移,单侧腺叶切除对于小的、单发的、腺内型的甲状腺癌是足够的(强烈推荐,中等级别证据)
表2分化型甲状腺癌(4cm)甲状腺全切与单侧腺叶切除的获益比较
经过合理的选择后,对于那些局限于甲状腺内且肿瘤直径为1-4cm的DTC患者,甲状腺全切与否可能与总生存期的提高并不相关,但在某些情况下依然有充分的理由考虑将双侧甲状腺全切术作为初始治疗。根据ATA指南第35B条推荐,如果诊疗团队根据术前评估及患者个人意愿判断该患者术后需行I治疗,则应首选甲状腺全切术。该推荐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可充分结合当地诊疗团队的诊治理念及患者意愿,综合判断单侧腺叶切除术是否是患者的首选初始治疗方案。由于乳头状癌具有多灶性的特点,甲状腺全切比单侧腺叶切除的复发风险低。但在经验丰富的医疗中心,合理把握适应证,结合术前高质量的检查及良好的临床判断,单侧腺叶切除的局部复发率也可低于1%~4%[7,12-14]。此外,对于那些在随访中出现局部复发的少数低危患者,行补救手术治疗同样有效,且可取得相同的良好长期预后。当然患者也应理解,根据术中及术后发现,单侧腺叶切除术根据需要转变为甲状腺全切术;患者也应支持手术医师根据术中发现而临时改变手术方式。但必须强调的是,单侧腺叶切除作为初始治疗方式是否合理应根据术后1~2周后的最终病理报告而定。仅有约5%~6%的患者需在单侧腺叶切除后早期即完成甲状腺全切[7,12-14]。但对于那些倾向于对具有中危特征的患者行I治疗的团队而言,单侧腺叶切除后早期即完成甲状腺全切的比例可达20%[15-17]。根据已发表的一个用于极低危甲状腺癌积极监测的临床决策体系,综合考虑3个重要的且互相联系的因素可以帮助决定患者是否将单侧腺叶切除作为首选初始治疗方式[18]:即术前影像学检查和临床发现以及医疗团队和患者自身因素。术前影像学检查和临床发现。仔细回顾患者的术前颈部超声、病史及体格检查等资料,如发现肉眼可见的腺体外侵犯、局部转移或远处转移,均应推荐行甲状腺全切;如发现对侧腺体内多发结节或术前超声发现较多的非特异性表现(如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或不典型的颈部淋巴结),则更倾向于推荐行甲状腺全切,以利于术后随访的有效开展。
有经验的多学科处理团队在决策过程中将良好的临床判断与高质量的术前颈部超声检查相结合,单侧腺叶切除术作为初始治疗方案的成功性可得到显著提高。然而在缺乏高质量的颈部超声检查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对异常颈部淋巴结的评估不够准确时,单侧腺叶切除的选择就难以明确。医疗团队因素。
了解当地医疗团队对术后组织学提示异常但术前评估并无明显发现的中危患者(如微小腺体外侵犯、微小淋巴结转移以及血管侵犯)术后是否行I治疗的态度是很重要的。如果医疗团队更倾向于对中危患者术后行I治疗,则他们就比那些对I治疗更加保守的团队更倾向于初始就行甲状腺全切术。这样的理念并非拒绝将单侧腺叶切除作为患者的初始治疗方法,但患者应理解根据术后病理情况有可能需要尽快再次手术,以完成甲状腺全切以便于术后随访。患者自身因素。
目前很多患者都积极参与治疗决策的制定过程,他们可以充分了解手术治疗的利弊。那些医疗激进主义者更加倾向于进行甲状腺全切(通常也支持术后常规行I治疗)[19];而那些医疗极简主义者则常常选择单侧腺叶切除,他们希望保留对侧腺体的功能以便可能不用终身服用甲状腺素。他们愿意接受将来还需要进一步治疗的可能性,但不接受一开始就进行积极治疗,尽管积极治疗可能预后更好。同样,他们对于术后早期发现以及治疗较小病灶的积极性并不高,因此也不需要术后的高灵敏度随访。所以,医疗极简主义者通常对患者进行低强度治疗即采取相对保守的治疗方法。总之,在缺乏确切证据证明肿瘤直径为1~4cm且分化良好的甲状腺癌行甲状腺全切术作为初始治疗可以有效提高生存期时,在合适的患者中,单侧腺叶切除将持续作为一种可选择的手术方式存在。合理选择患者行单侧腺叶切除时,应充分结合术前高质量的评估、医疗团队的理念及患者意愿。整合这3个重要因素后,相信每例患者都可以接受最适合的初治方案及术后随访。甲状腺癌术前影像学检查应如何推荐?
争议:甲状腺癌术前是否需避免行含碘造影剂的增强CT检查。
立场1:甲状腺术前应避免行含碘造影剂增强CT检查,以避免术后I治疗的延迟。
立场2:对具有局部侵袭性病变或临床可见的颈部淋巴结转移征象的患者,应常规进行增强CT扫描,以优化手术方案及手术的完整性。术前使用合理的影像学检查来优化手术方案比术后早期行I治疗更为重要。
初始治疗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切除原发肿瘤、甲状腺包膜外侵犯病变以及临床可见的转移性淋巴结”[1]。因此,术前评估必须包括甲状腺以及颈部解剖影像学检查,以便合理规划手术计划。颈部超声被广泛用于甲状腺结节及颈部淋巴结的评估。NCCN和ATA指南均推荐对术前确诊或怀疑的甲状腺恶性肿瘤患者行颈部超声检查以评估颈部淋巴结情况(表3)。虽然广泛的双侧颈部手术可鉴别出70%~80%的患者存在微小淋巴结转移灶[20],而术前颈部超声确定可疑颈部淋巴结肿大可有20%~30%[21-26]。因此,术前常规使用颈部超声检查可能至少改变20%患者的治疗决策[21,23,27]。术前颈部超声的常规运用有利于初始治疗的完整性,从而降低复发率及提高术后I治疗的有效性。表3影像学检查以及实验室检查在术前分期中的作用[1]
除了常规应用颈部超声对甲状腺癌患者进行术前评估外,有时还需要进一步使用CT或MR等断层影像来获得更重要的解剖学信息[1]。如有以下发现,除了进行颈部超声检查以外,还需进一步行断层影像学检查:声音嘶哑、渐进性吞咽困难、肿块活动度差、咯血、喘鸣、肿瘤增大或进展迅速,超声怀疑大的腺体外侵犯及较大的颈部淋巴结转移等。如出现上述情况,颈胸部增强CT可作为常规推荐,因为淋巴结侵犯范围可从上颈部直至锁骨上区及上纵隔。与旧版ATA指南不推荐术前使用含碘造影剂不同,新版指南第33A条推荐提出,如果发现或怀疑相关危险因素,则可使用含碘造影剂进行增强扫描。毋庸置疑,使用含碘造影剂的术后I治疗将不得不推迟,但术前更准确评估解剖结构所来带的获益通常大于术后I治疗推迟数周所致的风险[1]。虽然ATA指南明确指出使用造影剂后尿碘通常会在4~8周后恢复至正常水平,但具体间隔多久才不会影响后续的I治疗疗效尚不明确;即使尿碘水平恢复正常,甲状腺组织中剩余的碘仍将影响I治疗。尽管如此,由于对甲状腺及局部转移性病灶进行全面彻底的切除在初始治疗中至关重要,高危患者在术前行增强CT扫描以优化手术方案仍相对合理。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术后I治疗延迟数月也是可以接受的,且并不会影响清甲治疗、辅助治疗以及清灶治疗的效果。除此之外,其他术前影像学检查很少被用到,除非患者的临床表现及体征提示存在远处转移性病灶。尽管18F-脱氧葡萄糖(fluorodeoxyglucose,FDG)PET显像在肿瘤分期和随访中具有显著价值,但对DTC,该显像仅局限用于I难治性患者,且很少用于术前评估[1]。术后I治疗的作用
争议:DTC患者甲状腺全切术后是否常规推荐行I治疗。
立场1:所有DTC患者甲状腺全切术后均应推荐行I治疗(腺体内乳头状微小癌除外)。这有利于延长疾病特异性生存期,降低复发,还有助于初始分期以及提高术后长期随访时相关检测的灵敏度。
立场2:应基于个体化评估,选择性地进行术后I治疗。评估因素包括:疾病复发风险、疾病特异性死亡风险、术后疾病状态、对临床预后的重要性、术后分期的需求、术后高灵敏度随访的需求、治疗不良反应、医师的治疗理念及患者个人意愿等。
术后I治疗应如何推荐仍是DTC患者临床处理中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为了进行合理的讨论,I治疗的目的分为:清甲治疗、辅助治疗以及治疗已知的残留或复发病灶3类(表4)[29]。需要注意,辅助治疗是针对风险的,而不是针对明确的疾病,所以一部分患者在行I辅助治疗时可能已通过初始手术治愈。因此,在选择行I辅助治疗时应同时评估患者复发风险或疾病特异性死亡率以及该治疗使得患者在以上指标上获益的可能性。表4分化型甲状腺癌I治疗的目标[1]
目前文献存在的一些问题很难明确阐明I治疗是否对患者的复发或疾病特异性生存期有积极影响(图1)[30]。因此,很多指南对中危患者给出的是笼统的推荐,而对低危及高危患者给出的推荐则相对比较明确。图1目前文献存在的一些问题。很多因素使得很难从大量的回顾性以及观察性研究结果中得出关于I治疗的最佳使用方法[30]
对于术后是否需要行I治疗,ATA指南特别强调需要对术后患者进行仔细评估,从而决定是否需要进一步治疗或检查(表5)[1]。通过评估可确定I治疗目的是清甲治疗、辅助治疗还是治疗已知的残留或复发病灶,从而根据结果进一步决定I治疗的剂量。表5术后疾病状态在分化型甲状腺癌I治疗决策中的作用[1]
尽管ATA指南完全认可术后疾病状况作为治疗决策过程中关键因素的重要性,但临床医师考虑清甲治疗或辅助治疗的建议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ATA和TNM分期的风险分层(表6)。然而,ATA指南也认识到,在标准临床病理特征之外,其他相关因素,如术前和术后超声评估的质量、Tg测量的有效性及质量、外科医师的技术和经验、当地医疗团队的临床理念等,也应考虑在术后I决策中[1]。此外,ATA指南中第51A和51C推荐(表6)也强调患者的意愿在I治疗决策中很重要。从临床实践的角度来看,至少需要评估9个关键因素来确定术后I治疗是否对患者有益,包括:疾病复发风险;疾病特异性死亡率;术后疾病状态[包括抗Tg抗体(anti-Tgantibodies,TgAb)是否存在];对相关结局产生重要影响的可能性(复发、疾病特异性死亡率);对初始分期有显著改善的可能性;对高灵敏度随访的需求;治疗的不良反应;患者的意愿;其他相关因素,包括超声评估、Tg测定的质量、外科医师的技术经验和医疗团队的临床理念等。对那些在初始手术后没有任何持续性疾病存在的低危患者,这种管理方法通常会建议进行观察即可,而对大多数高危患者建议行I治疗,包括辅助治疗或清灶治疗(表6)[1]。对于中危患者,则应考虑行I治疗(第51D号推荐,表6)。中危患者是否推荐I治疗依据于对患者复发风险、疾病特异性死亡率及术后疾病状态的仔细评估。许多中危患者可能存在小的结构性病灶或异常的术后Tg水平,这些都提示疾病持续存在,这些患者是I治疗的潜在人选。如果术后评估没有发现生化或结构性疾病的证据,则应考虑行清甲或辅助治疗是否合适。如果中危患者的疾病复发率小于5%,应考虑观察或行清甲治疗以有助于分期和随访。对于高危患者,则考虑进行辅助治疗以降低复发风险,并根据肿瘤对I治疗是否有反应来提高总生存率。这些因素均应整合到患者治疗的决策过程中,包括复发风险、疾病特异性死亡风险、术后疾病状态以及辅助治疗获益的可能性等。表6术后I治疗在分化型甲状腺癌治疗中的作用[1]
对于I治疗剂量的选择,ATA指南推荐MBq作为低危患者清甲治疗的合理选择(第55A推荐,表7)[1]。如治疗目标为辅助治疗,则推荐使用更高剂量。遗憾的是,目前文献并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来明确辅助治疗的最佳剂量。因此,根据专家意见,辅助治疗的推荐剂量为~MBq,具体剂量取决于上面提到的多种因素以及医疗团队的临床理念(第55B和56推荐,表7)。对于已知存在持续或复发性疾病的患者,除了老年患者一般最大剂量不超过MBq外,I治疗剂量建议为~MBq[1]。表7I清除残留甲状腺组织(清甲)治疗、辅助治疗以及清灶治疗时的剂量推荐[1]
结论
甲状腺癌的临床处理尚有较多争议,但在很多方面已达成普遍共识。只有深刻理解相关决策及推荐背后的基本逻辑与原理,包括初始手术的范围、术前影像检查的完整性以及I治疗的作用,临床医师才能更好地理解每个复杂问题中的独特观点。这样的理解还将使我们进一步明确未来研究的方向,以便进一步完善指南。最后,只有通过积极主动、目的明确以及包容性强的多学科合作,这一领域才能逐步向前推进,才能使我们对每例甲状腺癌患者的治疗和随访达到最优化。(其余略)
中国医师协会核医学医师分会科普与信息化工作委员会科普与翻译组
上海交通医院罗全勇教授校稿
首都医科医院李春林教授终审
附注:本文已发表于年第12期中华核医学与分子影像杂志
(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