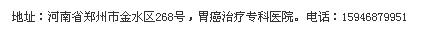作者:叶润仪王深明
文章来源:国际外科学杂志,,44(02)
精准医疗,是以个体化医疗为基础、随着基因组测序技术快速进步以及生物信息与大数据科学的交叉应用而发展起来的新型医学概念与医疗模式。年初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提出此计划,并很快得到医学界的普遍重视。精准医疗的核心内容是通过基因组、蛋白质组等组学技术和医学前沿技术,对于大样本人群与特定疾病类型进行生物标记物的分析与鉴定、验证与应用,从而精确寻找到疾病的原因和治疗的靶点,并对一种疾病不同状态和过程进行精确分类,最终实现对于特定患者进行个性化精准治疗的目的,提高疾病诊治与预防的水平。甲状腺癌是内分泌系统中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约占全身恶性肿瘤的3%。近30年来,甲状腺癌以6.2%的年增长速度递增,成为当前增长速度最快的恶性肿瘤[1],我国流行病学资料[2]也显示,甲状腺癌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发病率由年的1.78/10万升高至年的6.56/10万。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临床领域中的应用,甲状腺癌发生、发展、转移及预后相关基因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为甲状腺癌的精准治疗建立了良好的基础。
1 常见的甲状腺癌相关基因
在甲状腺癌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多种癌基因与抑癌基因参与其中,目前已经确定的有B-RAF癌基因(BRAF)、ras癌基因(RAS)、RET/PTC重排基因(RET/PTC)和特异性结合域转录因子/过氧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融合基因(PAX8-PPARγ),这4个不同基因的改变与甲状腺癌的诊断和治疗关系密切,其他包括p53、HIF-1α、Wnt/β-catenin、microRNA、NF-κB、PI3K等相关基因与甲状腺癌的关系也正在研究当中[3]。目前发现与人类肿瘤相关的BRAF基因突变约65种,其中BRAFVE(TA点突变)是甲状腺癌最常见的基因突变。RAS突变是仅次于BRAF突变的次常见突变基因,在甲状腺滤泡状癌中占40%~50%,在滤泡性乳头状甲状腺癌中占约10%(滤泡性变异型),在滤泡型腺瘤中占20%~40%[3]。在儿童散发性甲状腺癌病例中,RET/PTC重排发病率约45%,高于成人;而在辐射后的甲状腺乳头状癌中重排率远高于散发性的病例,可达60%~70%[4,5]。PAX8/PPARγ重排可以作为甲状腺滤泡状癌特征性诊断性标志物,但也可见于很少的甲状腺乳头状癌和滤泡状腺瘤中[3]。
2 分子标志物协助诊断甲状腺癌
高分辨超声是诊断甲状腺癌最重要的辅助手段,结合超声的甲状腺细针穿刺细胞学活检(Fineneedleaspirationcytology,FNAC)是目前术前鉴别甲状腺结节性质最有效的方法。但由于操作者的熟练程度和细胞病理学检查水平的要求,很多病例呈现假阴性而不能明确诊断。因此,针对FNAC不能确诊的甲状腺结节,很多学者提出通过检测甲状腺组织或者甲状腺细针穿刺样本中的甲状腺癌分子标志物来协助诊断。
最新版美国甲状腺协会(AmericanThyroidAssociation,ATA)指南建议:不能确诊的患者可以检查分子标志物,包括BRAF、RAS、RET/PTC、Pax8-PPARγ。意义不明的非典型性病变(Atypiaofundeterminedsignificance,AUS)、意义不明的滤泡性病变(Follicularlesionofundeterminedsignificance,FLUS)或滤泡性肿瘤结节(Follicularneoplasm,FN)若存在RAS突变有84%可能是恶性的。有BRAFVE、RET/PTC、PAX8/PPARγ突变的AUS、FLUS、FN或怀疑为恶性的结节恶性病变的风险大于95%。
目前能有效检测甲状腺癌的分子标志物主要包括RAS、PIK3CA、PTEN、P53、ALK和BRAF基因突变[6],而P53、ALK突变只发生在低分化癌和未分化癌[7]。AKT1突变只发现在甲状腺癌转移灶中,甲状腺原发的癌组织中并不存在[8]。RAS、PIK3CA和PTEN突变共存于甲状腺癌中,且与甲状腺癌的恶性程度相关[9,10]。相对于单独的基因检测,研究显示对多个基因进行联合检测比单一基因检测能够显著提高诊断率。
3 分子病理特征与甲状腺癌的预后复发关系
版ATA指南特别强调了规范术后病理报告对准确分期及术后治疗决策制定的重要性,也指出了目前TNM分期系统的不足之处。TNM分期系统未能将病理组织类型、BARFVE和端粒酶反转录酶(Telomerasereversetranscriptase,TERT)等的分子特征、远处转移部位及数目、转移病灶功能状态及初始治疗的有效性等与肿瘤死亡相关的因素纳入评估范畴[11]。研究发现BRAFVE基因突变不仅通过异常激活MAPK信号转导通路,参与甲状腺乳头状癌的发生、发展[12],而且与甲状腺乳头状癌的多灶性、包膜浸润、淋巴结转移、较晚的TNM分期等侵袭性病理特征以及复发、肿瘤相关死亡密切相关[13]。
但也有研究认为,BRAFVE突变预测复发的灵敏度(65%)及阳性预测值(25%)较低,还不足以作为独立因素纳入复发风险评估体系[14]。目前,指南仅将BRAFVE基因突变与肿瘤大小、腺体外侵犯等特征相结合纳入术后复发风险评估体系。TERT基因突变虽然是分化型甲状腺癌(Differentiatedthyroidcarcinoma,DTC)的肿瘤相关死亡的独立预测因子(HR=10.35),且与BRAFVE突变同时存在时疾病复发率更高[15],但因证据相对较少,指南暂未将其纳入复发风险评估系统。
4 基因检测与甲状腺癌的治疗
4.1 基因检测与甲状腺癌的外科治疗
最近进行的一项通过细针穿刺细胞学活检(Fineneedleaspirationcytology,FNAC)进行BRAF、RAS、Pax8-PPARγ和RET/PTC分子检测以确定甲状腺手术切除范围的研究显示,FNAC分子检测有助于区分哪些病例需要进行甲状腺全切除术,而哪些病例的切除范围可限制在腺叶内,包括良性甲状腺肿瘤及甲状腺乳头状微小癌。对于无淋巴结转移的低危DTC,是否行甲状腺全切除或单侧腺叶切除以及是否行预防性中央区淋巴结清扫依然是外科医师争论的焦点。BRAF突变增加了甲状腺癌复发的再手术率,复发患者的中央区淋巴结中BRAF突变占78%~95%[16]。
所以,BRAF突变阳性的甲状腺乳头状癌患者在行甲状腺全切除同时应该进行预防性中央区淋巴结清扫。对甲状腺乳头状微小癌的外科治疗目前有较多的争议,有学者认为应该行甲状腺全切除术,甚至预防性中央组淋巴结清扫。也有学者认为仅行腺叶切除或部分切除即可。甚至有学者提出无需手术,因为许多病例终生携带甲状腺癌而并不危及生命。如何鉴别这些病例是否高危,未来相信通过精准医疗的实施,一定会有一个明确的个体化治疗方案或指南的产生。
4.2 基因检测与甲状腺I治疗
病灶具备摄碘能力是决定I治疗疗效的前提条件,BRAFVE基因突变可导致碘代谢相关基因的表达下降,一项研究[17]发现BRAFVE基因突变组的远处转移灶摄碘率明显低于基因野生型组(15.8%vs94.4%),且经I治疗后突变组患者更易出现血清学进展(血清甲状腺球蛋白水平无明显下降甚至出现升高)。摄碘较好的转移病灶RAS基因突变率较高,然而RAS基因突变患者并未被证实可获得更好的I治疗疗效[18]。版ATA指南首次提出了BRAFVE基因特征对I治疗决策的潜在指导作用,但由于缺乏大样本随机对照研究以及伴远处转移的中、高危患者的研究证据支持,尚未常规推荐在I治疗前对BRAFVE基因进行检测。
4.3 甲状腺癌的靶向药物治疗
目前甲状腺癌的分子靶向治疗药物主要包括针对血管内皮生长因子靶点、针对原癌基因RET、针对BRAF基因、针对EGFR靶点的药物,其中2种针对BRAF的靶向药物索拉非尼(Sorafenib)和乐伐替尼(Lenvatinib)已成功上市,分别于年和年被美国FDA批准用于局部晚期或放射性碘难治性的转移性DTC的治疗。其他针对RET/PTC、PAX8/PPRγ突变的靶向药物,多处于临床试验测试的不同阶段。靶向治疗针对常规治疗无效且处于进展状态的晚期甲状腺癌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手段,能够改善晚期甲状腺癌患者的预后生存期,有良好的发展和应用前景。
5 甲状腺癌精准治疗的临床现状和展望
甲状腺癌的精准治疗目前还没得到广泛的应用,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分子标志物的检测技术、基因突变的筛查医院的开展,而且不少技术目前国内还没能够开展,部分技术只能够在实验室进行,未能在临床上应用;即使在临床中已应用的技术敏感性与特异性仍不够高。其次,临床医师对精准医疗观念的不熟悉,加上常规治疗手段对大多数甲状腺癌患者的疗效非常好,导致对这些新技术的应用推广不感兴趣。但是,精准医学是依托现代科学技术和生物医学,通过明确诊断、全面评估病情以及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法,给予患者以个体化、针对性的治疗,可大大改善个体患者的临床预后。随着技术的进步,甲状腺癌分子层面研究更加深入,基因检测技术更加敏感和更具有特异性,且更加简便以及靶向药物的多样化及有效性的提高,精准医学在甲状腺癌的诊治过程中一定会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FIS(10周年)强势来袭!
点击图片!报名参会投稿啦!
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