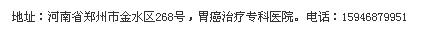左秦注:
篇幅较长,计一万言。写得细致、深入。不拘泥于一首诗之评读,更想能够写出自己对诗之体悟。评诗即为了探寻好诗之标准。
好诗有标准吗?肯定有。但绝对没有放诸四海皆准的标准。但,有一些基本的美学理念,却是每首好诗都应该满足的。
现代诗,让人迷茫,我也迷茫。我因为迷茫所以写评。里面的所有思想都是我一步步领悟、总结、整合的,希望对诗友有所帮助。
我爱诗如命,不希望诗受到不公对待。诗歌振作,诗人振作。
诗歌之未来,诗人之未来,必然是光明的,因为有着无数诗歌热爱者存在!
开着火车去拉萨
开了一辈子的火车
来江西援建铁路的同学
病的病,死的死,黯然下车
欢送会上
领导问司机张大民
退休后有什么打算啊
他憨憨一笑,说
我想
开着火车去拉萨
同事们一听都乐了
他一脸肃穆地说
我要在布达拉宫广场下跪
为你们祈祷
然后
再开车回来
.12.3
左秦评:
火车是水笔最喜欢用的意象,也许跟他曾经做过火车司机有关。
这首诗写得很小说,结尾是很典型的欧亨利结尾。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
诗意的营造不仅来自于意象的碰撞,而来自于戏剧性和反差。
“我要在布拉达宫广场下跪/为你们祈祷/然后/开火车回来”
同事们听了这句后,肯定立马会“异常安静”。
傻人有至福,傻人有至善。心无旁骛,唯有对亲朋好友之爱也。
口语诗多写人,写寻常之人缺少典型。
为何很多口语诗水了,所写人物不典型,所以事件不典型。
此诗的张大民可谓典型也。再加之写异常之人本来就有异常之感。
异常者,即诗也。
喀什的夜晚(节选)
不上网的夜晚
我就数星星
这里的星星比老家多,而且更亮
它们彼此遥遥相望
冷漠一辈子
直到
地上的人们死了一茬又一茬
换了人间依然璀璨
左秦评:
水笔这首五段共四十五行诗,我只截取他最后一段。
为何?叙事过于拖沓,将其多余叙事节省了,诗反而更加内敛、智性。
口语诗,是成也叙事败也叙事。
叙事是水,使诗更加滑润、通透、灵动,但叙事太多了,诗就水了。
诗的张力来自意象之碰撞和戏剧性。
口语诗张力多来自戏剧性,戏剧性也即诗的反常,或者说荒诞。
荒诞叙事、省略叙事、虚拟叙事,才是叙事的好法子,事无巨细,或者盘根错节,未尝好用。
如果读者想读故事,会去读小说,为何纠缠于诗不放呢。
诗里的猎奇、幽默等,都不能与其他文体相比,故而钻营此类为己任,终究不是好路子。
水笔的《谁叫他撞到枪口上》被我思考再三舍弃了,就是因为叙事过于平淡无奇,甚至还有拗口的地方。我之所以会纠结,是因为结尾的三句诗:“这里暗无天日/你那点儿光/连自己都照不亮”。
有诗人说要去除警句,完全用“朴实无华”的句子,通过所叙事之张力来构造全诗。
但殊不知,这样为之,诗味是寡淡的,读者也不能很好地整合出你之所表达。
夜晚没有几颗亮星子终究是无聊的。这亮星子其实就是警句。
水笔这警句用的好,而且本身也有机趣,可惜整首诗的叙事稍微差了一点。
有人说伊沙的诗是在抖机灵、抖包袱,这机灵、包袱就是机趣,但有时抖的不是地方,故而有人不喜欢。
我时常看到一些矫情的口语诗,矫情处即是抖机灵和包袱处。
平淡无奇的叙事忽然出现“孤独”“绝望”等大词,用力就过度了。
有句有篇,即句高度嵌合于诗篇也。
嵌合一词,说出了诗人的匠心,别说任性而为,那是高境界者为之。你默想,自己境界高超吗?
《喀什的夜晚》最后一段意境十足,但意境已经是烂大街的事,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意境写个鬼。
就是不会写诗的普通读者都会写出几句有意境的诗。故而,不要用意境唬人。意境乃人人可以为之。但意境是否嵌合诗篇,却需要一定功力。
此处意境之重实际在于“星子比老家多”,这里的数量之分引出了结尾两句相当惊人的警句。
很多警句都是可以通过练习、琢磨句子结构模仿出来的,但有些警句却是富含着诗人的人生经历、思想深度。比如这句:“地上的人们死了一茬又一茬/换了人间依然璀璨”。
至于此句之美妙,读者朋友一读便知。
无通感,无异质混成,无玄学气,但依然是一流诗句。
何也?我想就是其人生与哲学的融合吧。
金贸大厦
每次走到门口
保安都要打量我半天
虽然
我穿着不像民工
每次爬到三十七层
都被人挡回来
他们不相信
我是来锻炼身体的人
他们希望我坐电梯
但是
我是民工
收入少,闲工夫多
我有的是时间
为什么不可以选择爬楼呢
在这个陌生的城市
只有
这栋牛逼的高楼
让我蠢蠢欲动
总有一天
我会骑在它的头上
对脚下的蚂蚁说
我一口唾沫
就能砸死你们
左秦评:
这首诗其实把“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处腰斩了而独立成诗也同样可以。如:
《金贸大厦》
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只有这栋牛逼的高楼让我蠢蠢欲动总有一天我会骑在它的头上对脚下的蚂蚁说我一口唾沫就能砸死你们
我钻营于写短诗,就在于打通诗歌内部所有关节,不给诗留下一点破绽出来。
有人说留下破绽、引敌深入,故意写差、引人深思,纯粹是瞎扯淡。
喜欢辩解的人,都是冥顽不灵、狂妄自大之人,这其中就包括部分的我。
把诗当做人来写。人是独一无二的“精密仪器”。
我鉴赏韩敬源那首《儿时同伴》时说“坐在水中/低头修表”的“表”有着很深的诗学价值,就在于“表”是精密仪器也。
科学和艺术的一大区别就在于艺术主观、科学客观。
有一个量子物理学家他放弃绘画专攻物理的原因就是不能忍受绘画的不严谨、太任性为之,没有镣铐束缚,写诗是无趣的。
专心经营一首诗,不要想着写长,写成大作。要知,小处完美者,整体才会完美。
水笔的这首诗我之所以腰斩,并非诗未打通,而是个人觉得,将其腰斩了,也许诗意更加集中,更加小巧、奇特。
此诗之表达可谓“苦中作乐”也、装逼也、幻觉也。
登上山顶我为峰,那种虚幻的感觉,确实让人豪放:登泰山而小世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至于此诗将楼下生灵称之为“蚂蚁”,是否不道德,这不是诗要考虑的事情。
诗,需要夸张。夸张同样是一张荒诞。
荒诞是对生活的解嘲也是无力反抗。
不荒诞而写生活,写了又有什么意思。
蝗灾
她们成群结队
挤上破旧的车厢
她们对新疆一无所知
也不懂劳务输出和农民工专列
对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她们只知道
新疆遍地都是棉花
雪白的棉花
等着她们去摘
就像饿坏了的孩子
抓住了母亲的乳房
她们冲出车站
爬上汽车,犹如饥饿的蝗虫
一阵风似的扑进棉田
每年农历八月
这些蝗虫
在祖国的西北部集结
一次又一次
回回都自生自灭
左秦评:
水笔善写大题材。大题材难写。
大题材,拼得是大题材所蕴含之领悟,但更是其对领悟的整合。
诗人不是哲学家,在社会问题中看到的并不比普通人看的更加深刻。故而诗人所写,依然是为苍生诉苦为苍生请愿也,而那些写成说理、乡土诗者,就是一种无效、庸俗的写作。
水笔《蝗虫》所写,不外乎是“以为走进了天堂,其实不过是去了其他的地狱”。
去新疆摘棉花,或者去广州打工,想以此来改变人生、脱离穷苦之地,但大多数人依然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就像饿坏了的孩子/抓住了母亲的乳房”
此句诗有夸大的嫌疑。其实粮食和乳汁,还是有所不同的。
人们在此时并不是爱棉花,而是没有了棉花就不能生存。很多人对土地也是如此,并非有多爱,实在是离不开。
母亲的乳房,是用烂了的意象。
于坚所说的拒绝隐喻,就是拒绝这种隐喻被用烂了的意象。
“她们冲出车站/爬上汽车,犹如饥饿的蝗虫/一阵风似的扑进棉田”
此诗诗题为《蝗虫》,蝗虫乃喻体也,也是此诗的中心意象。
蝗虫在此诗中相当奇特。结尾段的惊人之感,即来自蝗虫的发散。
但,将她们比喻成蝗虫这为害之物是否得当呢,我存疑。
庞华的本真诗意中有四点:准确、通透、集中、完整。
这首诗的喻体“蝗虫”定然是不满足准确之要求的。
去除这点缺憾,这首诗写得还是非常精彩的。
“每年农历八月/这些蝗虫/在祖国的西北部集结/一次又一次/回回都自生自灭”
至于此处的悲观气息过于浓烈就不多说了,因为大多数诗人都是悲观的。
用俗得烂大街的话来说就是:只看到道路的坎坷,却没看到前途的光明。
为何普通读者更喜欢彼岸诗人,因为彼岸虚幻也、有盼头也、美好也、陌生也。
写日常生活者,多发生活是无聊的、孤独的、绝望的之感。
置身生活中,更觉得生活之质感之冰凉也。
此诗结尾说“回回都自生自灭”似乎也有问题。
“她们”是并没有妥协的,她们每年农历八月依然会在祖国的西北部集结摘棉花,这就是她们的作为、不妥协。
潮
扎红头巾的女孩
坐在灶前
火苗探出头,将灶头熏黑
灶上的铁锅冒着热气
家徒四壁,番薯飘香
初冬的阳光
与去年别无二致
它们低头进门
停在土墙上,聚集在泛黄的报纸上
它们照亮了
这个衣衫褴褛的失学孩子
她滚圆的脸蛋
正慢慢地泛起红晕
左秦评:
这“初冬的阳光”点亮了整首诗。这首诗让我想起了一幅世界级名画《康乃馨、百合与玫瑰花》。
这幅油画是萨金特静心绘制的传世经典。
此幅画描画了两个孩子在花丛中点灯笼的情景。
灯笼挂在花枝上,灯笼为鲜花抹上了一层温暖的光芒也为两个孩子笼上一层温暖的光芒。孩子活泼健康的脸庞,被映衬了出来。
萨金特的画是温暖的,而水笔所写的《潮》则是冰冷的、悲凉的、苦难的、瘦削的、饥饿的。
萨金特的画有着古典美,灯笼里的光给人朦胧之美、含蓄之美,而水笔的诗则有着现实之痛,初冬的阳光照亮的是一个衣衫褴褛的失学孩子。
“她滚圆的脸蛋/正慢慢地泛起红晕”
此是一种希望的萌芽么?此是阳光给人的温暖么?
诗的第一段很有生活气息:“火苗探出头,将灶台熏黑/灶上的铁锅冒着热气/家徒四壁,番薯飘香”。
此处写得很温暖、温馨,尤其是“热气”让人对“初冬的阳光”更有感受。
灶台上散发的是热气,初冬的阳光,却有一丝冰凉。从热到冰,更觉其冰。
我更愿将“红晕”当做是“回光返照”,虽然这样未免太残酷了,但家徒四壁、衣衫褴褛、失学,又能给人多说暖心之意呢。
任何悲悯背后都有无声的控诉,任何悲悯背后都有对世界、命运的无奈。
一寸隐私
农民工不懂何为性工作者
也不懂什么叫隐私
他们只知道
老子花钱
就是来买快活
但是
当李建设在吕桂花身上
为所欲为
准备吻她耳根时
却遭到拒绝
她说
这块肉
一直很干净
我答应过男友
为他留着
左秦评:
评水笔的诗,谈诗艺都感觉没多大必要。
水笔并非技艺型诗人,多是心动情动而写。
诗艺上可能不完美,但所写之内涵却超技艺型诗人很多。
诗艺只是谋篇谋句的方法也,只是一张建筑图纸。
图纸好,固然是个好开始,但建筑所要之砖石、泥沙,更加重要。
技艺型诗人,多写得文采斐然、高深莫测,但往往却写得拥堵了闭塞了。为何?砖石泥石有所欠缺也。
水笔是诗人中的小说家,微小说诗之掌门人走召应该选录其诗。
水笔所写社会百态、各种不同阶层之人物层出不穷。
此首《一寸隐私》乃写性工作者之佳构也。
读到“她说/这块肉/一直很干净/我答应过男友/为他留着”岂能不动容?
谁想主动为妓为奴,多为生活所迫、情非得已。
吕桂花之坚守,乃耳根也。
耳根虽小,却有着对男友的承诺和爱意。
至于此处出现的“农民工”嫖娼问题和男友为何“纵容”吕桂花卖身之问题,无需多想,非诗之重点。
口语诗,尤其是走召提出的微小说诗,是应该满足微小说和诗的两个要求的。
诗和微小说高度融合,微小说诗就成了。
写诗不局限于诗,很必要。太执着反而害诗甚多。
命运
大干七八九,火车司机李建设
在下班路上猥亵幼女
被人揪到保卫股
愤怒的人说
畜生啊,千刀万剐
也不为过
事过三天
李建设背着党内警告的处分
继续上班
单位领导说
杀一个,少一个
都杀了,谁来开车啊
年
祖国大地上枪声四起
多少冤魂成新鬼
那年,铁路异常繁忙
全国工农业生产捷报频传
.3.16
左秦评:
水笔之诗,很多都特别大胆。大胆,不遵循伦理道德。伦理道德害诗久矣。
孔子一句诗无邪,后代之诗就缺少了邪魅之气,缺少了及物、人之在场。
很多诗都是闲适的白色写作,就是有着火药味、血腥味的红色写作,都缺少力度、惊世骇俗之笔力。
大胆,又荒诞。因为大胆,故而敢看,仔细一看,这个世界是如此荒诞。
表面写作,有何意思,只有深入,深入下去,荒诞即出。
这首诗的时点为。这年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时年的荒诞却可想而知。
李建设(注:此人民出现多次,已经构成了隐喻,“建设”者,何意,读者深思)猥亵幼女,是滔天之罪、该千刀万剐,但却只是背负警告之处分。何也?年已经改革开放,谋发展之际。促生产,谋利益才是关键,人之生死、伦理,又岂能挂碍。
曾经语文课本中说铁路之下,皆是工人之幽魂。
在人类的进步发展之中,黑暗、残酷之事,多得数不胜数。此即水笔所写之内涵。
“杀一个,少一个/都杀了,谁来开车啊”
此是水笔所写又一警句,可玩味之处很多,是歪理、诡辩乎?就是歪理、诡辩,正因为如此,才觉得深刻。
此诗的末段讽刺味十足,只是“祖国大地上枪声四起/多少冤魂成新鬼”是诗之败笔。
第一,失之直接、浅陋。
第二,李建设猥亵只是处分,并未枪决,而且文中已说“杀一个,杀一个”,何来的枪声四起。
第三,冤魂成新鬼,稍觉别扭,有文意不通之处。
白夜酒吧
我要说
那些来此买醉的人
根本不懂一个人的黑暗
那是灵魂里的黑暗,无人能点亮
而他们以啤酒主义者自居
在喧闹中嬉笑怒骂
用诗歌的方式
男欢女爱
并以诗歌的名义干了一杯
他们干了一杯又一杯
说的那些鬼话
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
他们习惯了
在午夜做白日梦
那个坐在黑暗中的人
始终不曾露面
她懒得写诗
洗洗就睡了
.1
左秦评:
写诗之人不知白夜酒吧者,都是半吊子。
翟永明开了一家酒吧,叫白夜酒吧,是诗人常聚集之地。
白夜,本身就是一个极好之意象。
诗题就给了我诗味扑鼻而来之感。
白夜酒吧,左秦今生,要去一次。拜访白夜永明,跟我的八十年代情怀有关。
切入正题吧,絮絮叨叨,是写诗之大忌,也是写评之大忌。
水笔这首诗很简单,通过列举然后对比来说明什么是“一个人的黑暗/那是灵魂里的黑暗,无人能点亮”。
此诗列举了买醉之诗人。贬义显而易见。
此类诗人嘻笑怒骂、男欢女爱、说鬼话、做白日梦,是插科打诨、无聊、沦落、胆小无能之辈。
诗人将诗分为两段,其实分为三段更加恰当。
第一段是引子、引线,第二段是反例,第三段是正例。
懂得一个人(的灵魂里)的黑暗的人是那个坐在黑暗中的人。
“她终不曾露面”,非天天聚会喝酒之徒。
独守一处、孤独自持、有诗写诗无诗慵懒而眠,不管世事、不入人世,得其所哉、居于幽暗。
“那个坐在黑暗中的人”在水笔心中,我想大概举的是翟永明吧。
只是这首诗有存疑之处,那就是,这样褒贬分明、对立分明,是否妥当。
并且,这样写,是不是太主观、用自己的一套标准打倒一片。
这首诗也是意境之诗,黑暗是其中心意象。
但“白夜酒吧”里写黑暗,是否好?
个人觉得,将“那个坐在黑暗中的人”色彩过于浓烈的意象“黑暗”改为“白茫”似乎更加妥当。
但如此为之,却不够准确,酒吧之类有“白茫”处吗?而且二元对立也不好。
故而不如将其改成“那个坐在霓虹灯之边缘的人”也许更好。
不知水笔意下如何?
露宿者
菲律宾没有梦想
马尼拉如此激进
规模浩大的美军纪念广场
黎刹公园
卡提可兰喧闹的街头
露宿者
睡意深沉,神态安详
他的梦想
他的激进
他的广场
他的国父
在喧闹中入睡
他睡在菲律宾的耻骨上
若他翻个身
就会让祖国蒙羞
左秦评:
记得曾经有这样一个对话。
我跟一个朋友说,你的写作青春化色彩过于浓烈,并且情感溢出明显、主观意识流动有失衡、崩溃之感。
那朋友说,其实我是有意为之(很多诗人都喜欢把别人指出的文本缺憾当做有意为之,其意很深),这种写法你不喜欢只是你走不通而已。
当时我竟无法反驳,现在我是不想反驳。
各安天命吧!固执己见之人,终是小器之人。
变无止境,时时将自己推翻,方能进步。谦虚领教,何乐而不为。
水笔为何取水笔之笔名,我还未问过。但我读其诗瞎扯淡一下:
水笔多指毛笔。
明陶宗仪《辍耕录.写山水决》里说“夏山欲雨,要带水笔。山上有石,小块堆在上,谓之矾头。用水笔晕开,加淡螺青,又是一般秀润画,不过意思而已。”
水笔作画,有水笔画之谓也。水笔涂抹社会百态,如同作画一般,可知其“水笔”之意也。
我之诗评体系里,多有“流水”一词。
诗如流水,贯通、流淌、滔滔而去、势不可挡。流水之笔,游刃有余。
笔力老练,无阻隔之感,握流水之笔,谓之“水笔”也。
左秦乃一唠叨小子。此评的两段都是一小感想,虽然于《露宿者》诗无涉,但却是我之点评与水笔之文风,有一定关系。
我为何评诗,不就因为很多人不懂诗、误诗、诋毁诗吗?
我之心意,希望大家体谅。
如若写评求名,我可以按大诗人目录一人写评,无需为一诗人写评几十篇。
好,不多絮叨了。
这首《露宿者》又是社会百态之诗作。
诗之前半部分写得如水平淡,是诗的引子、背景。真正有诗味、有机趣、有妙意的是后三句:“他睡在菲律宾的耻骨上/若他翻个身/就会让祖国蒙羞”。
让祖国蒙羞的是露宿者还是使之国民成为露宿者之人呢?意义自明。
此诗的高明乃“菲律宾的耻骨”和“蒙羞”之间的打通。
露宿者“睡意深沉,神态安详”跟“喧闹的街头”形成了对比
且露宿者之睡跟国父之“睡”又形成了一组关系。
诗,含蓄有致又见机心,很不错。
只是开头的“菲律宾没有梦想”有前置武断之缺憾,使诗显得主观。
此处应该还能再修改、润色一番。
时间会不会生病
住院后手机关了
手表也被护士没收了
医生说
手表是危险的东西
有了时间概念
对你的康复不利
是的,一个病人
要手表有什么用呢
而一个有时间观念的病人
对医生来说是
最大的麻烦
.2.17
左秦评:
我记得我暑假写我第一篇评时说,我写评之目的,就是找到好诗的标准。
我在寻找这标准的过程中,诗和评的水平都在不断提高。
现在对我来说,一首好诗第一应该满足诗场论。
诗场论者,我论述极多。此观点后来碰上庞华的本真诗意说,更加完善。
诗场论之要素即庞华本真诗意之要素:准确、通透、集中、完整。这是我衡量诗歌的初级标准。
满足诗场论了,算是艺术上的初步完美。但这还只是空壳而已。
我现在奉行的是肢体写作。直写人的肢体,故而人在场也、直接进入血肉骨也。
诗贵打通,捅破窗户纸,直接看到外面的世界。关节灵活,跟人一样可以行走。
再加之诗的反常、戏剧性、荒诞、境界,一首我认为的好诗就出来了。
至于意象、口语,都只是写法不同而已,没有特别的偏爱。
意象口语相结合,嵌合完美的,最得我心。
空谈标准是无用的,这也是我评诗的缘故。
纵你有完美至极的理论,没有实践、运用,都是空架子。
水笔这首《时间会不会生病》是一首存在之诗也。
诗之深度,我将其细分为时间深度、空间深度、情感深度、肢体深度、哲学深度。
实际上,时空深度,容纳了一切深度。
能写出时空感,或者直接写时空意象,诗都会有不一样的诗味儿出现。
玄学诗人的玄学气,多来自时空之营造。
水笔没有将“时间”写成玄学,而是用口语叙述出了一个跟“时间”有关的故事。
其实这首诗所写很像欧亨利的一篇小说:《最后一片叶子》
“瞧瞧窗子外面,瞧瞧墙上你最后一片藤叶。难道你还没有想过,为什么风刮得那么厉害,它却从来不摇一摇,动一动呢?唉,亲爱的,这片叶子才是贝尔门的杰作——就是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的晚上,他把它画在那里的。”
医生说手表是危险之物,因为有了时间概念,对康复不利。
那,为什么呢?
时间滴滴答答流逝,人的耐力、生命也跟着时间流逝。
人是时间生物,时间往往给了人很大的暗示、焦虑。
欧亨利小说里的叶子也是一样。等到最后一片叶子落下了,自己可能就要死了。
诗追求新。何蔚说“(新)指的就是作品的立意新,角度新,题材新,语言新,结构新等等,每一个‘新’都足以充当诗歌的保鲜膜”、
“新是兼容的,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它可以同时包含美,包含巧、奇、趣,也可以包含境、象和悟。”
诗之新,是何蔚所提的诗歌十项标准之首,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此诗的新就是诗的立意新。
“一个有时间观念的病人/对医生来说/是最大的麻烦”,这句诗,也许很多人都想到过,但很少能写出来。
至于诗的语言新,很难估定。口语、废话,应该是语言新之典范。
至于诗的结构新,最为冒险,很容易就写成了形式主义。
至于诗的题材新,很容易就写得猎奇、偏颇。